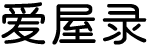田润叶从原西河畔回到学校以后,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——她的“牢房”。她感到胸口像压了一扇石磨似的沉重。
她躺在宿舍的床铺上,很快想到,明天就是清明节,殷勤的向前一家人,又会来缠磨她,让她去他们家吃饭。
少安没结婚之前,尽管她反感这种邀请,但也抱着“吃顿饭又能怎么样”的态度,勉强去了——这主要是为了她二妈一家人的脸面。可是现在,她绝对再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!
但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,她二妈又从旁劝说,她到时又可能没勇气和这一群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,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。
怎么办?
她从床铺上爬起来,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,牙咬着嘴唇,烦乱地抠着手指头。
她突然想起她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。丽丽和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同班同学,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。丽丽她爸原来是原西县文化馆长——去年晓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带着的。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地区文化局,当了副局长,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地区文化馆了。听说她现在编《黄原文艺》小报。丽丽爱好点文学,但也和她一样,不会写什么;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。润叶还听人说,丽丽已经有了男朋友,在地区团委当干部。
润叶想,这几天她也没课,干脆请几天假,到黄原丽丽那里去散一散心。同时,她也很想把她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,这样她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。这不幸只能给丽丽叙说,因为她了解她,也能理解她的痛苦。
她这样想的时候,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就起身。这样清明节她就不必呆在县城,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。
这个脱身计不错!好,明天一早就起身去黄原!
本来,她应该事先给丽丽写封信,告诉她要来,但现在来不及了。
她于是就草草率率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,准备第二天动身。
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,她回到二妈家,告诉二妈说,她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,写信让她一定赶清明节来一趟,因此她明天要去黄原。
润叶撒完这个谎后,她二妈遗憾地说:“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,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!”
“以后再吃吧!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,现在她得病住了院,我不去看一下,就太不近人情了!”
她二妈无话可说,只好同意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,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,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,动身到她的同学杜丽丽那里去了。
当汽车一从公路上奔驰起来,车窗外辽阔的山野、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时,润叶顿时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。她想:唉,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原西来,那该多好啊!原来她一直深深依恋故土,从来也没想过在外地呆个三年五载的。但现在她很愿意离开故乡,离开原西县城,到外地去不再回来!
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原城。她二爸当年在黄原工作的时候,她曾到这城市来过几次。她自己工作以后,也来这里为学校办过几回公务,因此对这城市并不陌生。不过,地区文化馆她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——自丽丽调到黄原后,她还没来过呢!
她出了汽车站,提着那个小提包,一路打问着,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。
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去过节,但一看老朋友来了,高兴地喊叫说:“你怎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?怎?给学校办事?”
润叶对她说:“我没什么公事。我想你了,就来看看你。”
丽丽说:“我也想你想得要命!我还梦见过你几次呢!而且在梦中,还不光是咱们两个人!”
“还有谁呢?”润叶问她的女朋友。
“还有你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!不过,你的男朋友可不是那个李向前!怎么样?没答应那个开车的吧?”
润叶苦笑着摇摇头。她本来此刻就想顺情一头扑在丽丽的怀里,向好朋友哭叙一番自己的不幸遭遇,但想她刚到,应该忍耐一下。她只是勉强装出笑脸,开玩笑问丽丽:“你的男朋友怎么样?敢不敢让姐看一下?”
丽丽调皮地扬了一下头,说:“他晚上准保来!你尽管看!也帮助我审查一下!”
润叶说:“我相信你的眼光······”
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,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。润叶也想上手,但被丽丽拒挡了,说:“现在你成了客人,不像咱们在原西县了!”在原西的时候,她两个经常一块做着吃饭,有时在小学她的宿舍,有时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。
两个好朋友吃完饭,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,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。
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她的惠良认识。
润叶一搭眼就知道,丽丽挑了个称心女婿。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,一副诚实相,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。
“你怎才来?”丽丽问她的男朋友。
“我一直在家等你呢!”惠良说。
丽丽笑了,说:“润叶来了,我就没去你那里······”
惠良马上对润叶说:“丽丽常说起你。虽然没见过面,我已经很熟悉你了。不知道你来,否则咱们一块去我家吃饭······”
“丽丽也在信上常说你的情况。”润叶对惠良说。
他们正随便说话,武惠良却突然变了脸色,说:“你们知道不?今天天安门出事了!我刚听完联播节目,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总理,进行‘反革命活动’,说公安局都出动了,看样子抓了许多人······其实,这再明白不过了!我刚还和几个同学议论,这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!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如《国歌》里唱的,已经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!人民都成了反革命,而真正的反革命却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,在人民头上舞棍弄棒······”武惠良激动地说着,手在空中挥着,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。
这惊心动魄的消息,使润叶和杜丽丽都感到无比震惊。听着武惠良激动地议论,润叶早已把自己的不幸搁在了一边。是啊,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公民,当国家出现不幸的时候,个人的不幸马上就会自动退到次要的位置。
他们三个立刻开始议论起眼前国家的不幸状况来。他们正当年轻之时,一个个热血沸腾,甚至指名道姓骂起了江青!
正在他们愤怒地议论的时候,门里突然进来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人。这人三十多岁,脸色黝黑,穿一身邋遢的衣服,头发零乱地飘散在额头。他进门以后,先打量了一眼润叶。
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。丽丽对润叶介绍说:“这就是我们馆的贾老师!”
“贾冰。”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点头,自我介绍说。
尽管润叶马上知道这就是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,但丽丽当她不知道,又立即给她补充说:“贾老师是大诗人!我们《黄原文艺》的主编。他常在报纸 上发表诗歌哩!你记得不?咱们以前还在原西朗诵过他的诗哩!”
润叶拘谨地说:“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······”
“听你口音也像是原西人?”这位诗人问她。
“我是石圪节公社的。”润叶告诉贾老师。
“噢,那咱们是老乡!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······对了,去年丽丽他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,他们说也是石圪节的。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······”
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:“这就是她姐!”
“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,叫田晓霞。”润叶说。
“噢,是这样!你二爸我认识!福军是个好同志!有头脑!有胆识!你们是?”贾冰指着润叶问丽丽。
丽丽立刻说:“我和润叶是老同学,最要好的朋友!”
“噢,那我就不怕了!”诗人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,说,“我刚写了一首诗!惠良,丽丽,还有这位老乡,你们听一听!你们大概也听广播了,他妈的,把人肺都气炸了!我亲爱的祖国!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,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······”诗人在未朗诵他的作品之前,就已经激动起来了。
贾冰展开稿纸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准备朗诵。润叶、丽丽、惠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,等待他开口。
一刹那间,诗人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,右手在空中扬起来,大声朗诵道——
今儿个,清明节刚刚过罢,
我,怀念
天安门广场上,那一朵朵
浸透了血泪的白花。
残雪,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?
乌云,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!
我们的民族,是滔滔的黄河,
历尽磨难,
奔涌在英雄的华夏······
镇压,怕什么?!
死,又怕什么?!
阳坡上有草要返青,
背洼洼有树要开花!
野火烧不尽,
冰雪压不垮,
革命人,一代接一代,
头掉了,不过碗大个疤!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诗人越朗诵越激动,到结束时,双拳挥舞,泪流满面!丽丽一边抹眼泪,一边轻声插嘴说:“贾老师,声音小一点,小心外面有人······”
贾冰像是回答丽丽,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自己最后的诗句——
让他们来吧,
我不怕!
我们不怕!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